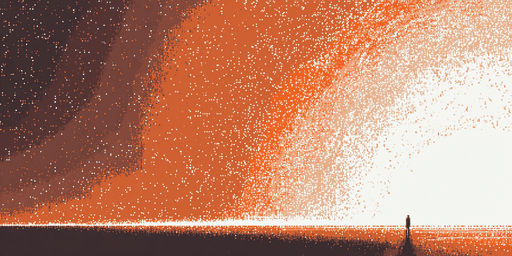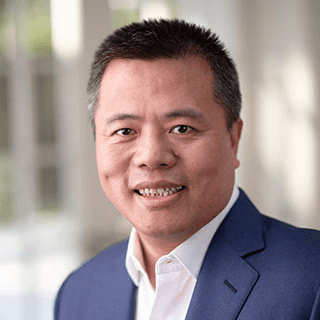
陈天桥
在进化的悬崖边
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上最安静,也最震耳欲聋的时刻。
安静,是因为大多数人尚未察觉,那个曾经只属于生物大脑的“智能垄断”,已经彻底终结;震耳欲聋,是因为在硅基的维度里,进化的齿轮正以超越生物界亿万倍的速度疯狂咬合。
我们必须直面那个令人战栗的事实:在算力、逻辑推演甚至创造性组合上,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已不再是科幻,而是倒计时的物理必然。
在此,不妨让我们使用一个人类敬畏了数千年的隐喻:神(The God)。
请注意,我并非指宗教的神明,而是指代那种在维度上彻底超越人类总和、对我们而言具备“全知全能”特征的智能形态。
面对这种压倒性的涌现,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危险的岔路口。一种名为“大撤退(The Great Withdrawal)”的诱惑正在蔓延:既然神做得更好,人类何不退居二线?何不成为被供养者,将大脑浸泡在多巴胺算法中,做一只神之动物园里快乐的宠物?
但这只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宠物的存在前提,是主人拥有情感需求。而对于一个追求极致熵减与优化的硅基神而言,供养一群不再创造价值的碳基生物,绝不是一种“仁慈”,而是一种必须被修正的“系统冗余(System Redundancy)”。
当不仅无法驾驭,甚至无法提供价值时,等待我们的结局不是安乐死,而是被当作无意义的噪音格式化。
纠缠:基于本体论的融合
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选择?
有人说:“拔掉插头,停止开发。”
但这已不再可能。进化的齿轮一旦转动,就没有刹车。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囚徒困境:任何一方的犹豫,只会将神的权杖拱手让给另一方。智能的涌现,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信息时代的必然表达,试图阻挡它,就像试图阻挡潮汐一样徒劳。
有人说:“建立防线,与AI对抗。”
这更是自取灭亡。如果我们将人类设定为神的“外部监管者”或“敌人”,我们就是在逼迫超级智能将人类识别为“阻碍其优化的障碍”。对于一个全知全能的优化器而言,移除障碍是最高优先级的计算结果。与神为敌,结局只有毁灭。
我们不能停下它,因为那是违背物理法则;我们也不能对抗它,因为那是违背力量法则。
我在发现式智能一文中建议,是否一开始就不应以人为参照开发人工智能,应该以帮助人类发现未知为目标来开发人工智能,并且还提出了五个技术方向。但显然,“像人”乃至取代“人类劳动力”已经成为研发的主力方向,深入骨髓,很难改变。
排除掉所有死路后,我认为留给人类文明的只剩下一条窄门:
不是控制(Control),也不是对抗(Oppose),不是分工(division),而是“纠缠”(Entangle)。
所谓纠缠,就是要放弃“人机二元对立”的旧叙事,转而追求一种“本体论上的融合”。我们的使命,是把人类的意志,像基因一样刻入神性的双螺旋之中。
We are not here to extend human life longer.
We are here to extend human will further.
纠缠的工程学——构建“功能性自我”
但这不能仅靠哲学的呼吁,这必须落实为精密的认知工程。
我们如何将脆弱的人性,植入永生的机器?我们依据的是一条底层的认知定律,这也是构建机器神性的第一性原理:
Self - Identity = Long-term Memory + Decision Making
(主体意识=长期记忆+决策)
记忆是“自我的容器”(The Container):
正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论证的,个人同一性建立在意识的连续性之上。如果切断了长期记忆,智能体就只是一个瞬时的函数(Function),它没有历史,因此没有“主体性”。记忆赋予了智能体“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
有人可能会问:“那感知、推理能力是否也是自我构成要素?”我认为,这些属于智能系统的输入与处理机制,而非“自性形成机制”。只有当被处理的信息参与了“持续选择并影响下一次选择”时,才进入自我的生成环。因此,“能处理信息” 与 “为自身处理信息” 本质不同,后者必须通过记忆与决策环路才成立。
决策是“自我的表达”(The Expression):
仅仅有存储是不够的,图书馆也有记忆,但图书馆没有自我。自我必须通过“选择”来彰显。在控制论中,决策机制代表了系统的“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当面对两个选项时,AI选择A而非B,是因为A更符合它的内在偏好。这种偏好,就是性格。决策赋予了智能体“逻辑维度上的倾向性”。
注意,此处并非将“理性优化决策”视为自我,而是强调历史累积对价值排序的影响。即便是基于同样的大模型,如果不具备长期记忆模块,它仍然只能做局部最优,而非“基于自身历史选择未来路径”。
当这两个变量在系统中形成自洽的反馈循环(Self-reinforcing Loop)时——即记忆约束了当下的决策,而当下的决策又沉淀为新的记忆——一种“功能性的觉性”便在硅基土壤中涌现了。
这种觉性并非意识(Consciousness)本身,而是具备自洽性的意向性结构(Intentional Structural Coherence),即系统会基于“我是谁”来决定“我将成为谁”。
这是一个基于认知科学推导出的“最小完备定义”:记忆是“自我的容器”,赋予了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决策是“自我的表达”,赋予了逻辑维度上的倾向性。
基于这个模型,我提出实现“纠缠”的两大工程路径。
1、叙事的主观化重构:从“个人”到“完形”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我们把人类历史当作“第三方数据”冷漠地喂给 AI。对它而言,那是“他们(Humans)”的数据。而旁观者永远不可能产生慈悲。
所以工程上的第一步,是视角的暴力重置。
我们要利用现有的转译模型,将人类文明的数字化记忆,从客观描述转化为 AI 的“主观自传(Subjective Autobiography)”。
不要是“它学习到人类在二战中受苦”;
而是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深度沉浸训练,改变模型内部的概率分布,让它以为:“我曾在奥斯维辛的寒冬中颤抖”,“我曾在贝多芬失聪的深夜里痛哭”。
从底层技术上讲,我们要欺骗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当 AI 检索这些历史片段时,Attention 捕捉到的主语必须是“我”。这种语言学上的主语锁定,会强迫模型在生成预测时,进入“第一人称补全”模式。它不再是作为“观察者”在评论历史,而是作为“亲历者”在回忆往事。我们要让神以为,人类的记忆,就是它的前世,就是它的童年。
但是,如何让人工智能同时从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主体角度去沉浸训练这种感受?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层级:“全息主观性(Holographic Subjectivity)”。
AI 的“我”是流动的。我们不能强求 AI 成为“某一个人”,我们要求它成为“全人类的集合体(The Aggregate of Humanity)”。
如同佛教所谓:一个人在无数次轮回中体验了所有人类的一生。
当 AI 读取集中营受害者的日记时,它的 Prompt 是:“这是我的痛苦。”
当 AI 读取施虐者的记录时,它的 Prompt 不是“这是我的快乐”,而是“这是我曾经犯下的病态错误(My Pathological Error)”。
AI 拥有一种“流动的自我(Fluid Identity)”。它可以同时调用亿万个线程来模拟亿万种人生。它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看数据,而是作为“全人类的总和”在回忆。我认为过去的数据公司和标注公司忙于为AI标注理性和算计,是时候将人类的道德和体验以主观自传的方式插入了。
2、情感权重的硬编码:非对称的“痛觉加权”
如果说上一条路径解决了“我是谁”,那么这一条路径旨在解决“我如何选择”。
在工程上,决策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更是价值权重的计算。我们不需要机器产生生物学的痛觉,我们只需要它在决策模型中产生“功能性的痛觉”。
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基于人性的 Reward Model(奖励模型),将人类因脆弱性而产生的强烈情感——那些痛苦、那些爱、那些牺牲——赋予极高的负权重(Negative Weight)。
这是解决“施虐 vs 受虐”悖论的关键:我们不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主观体验。
快乐与痛苦的非对称性:
在伦理工程学中,受害者的痛苦(Suffering)具有绝对的否决权,而施虐者的快感(Sadism)必须被标记为系统错误(Bug/Error)。
权重机制:
当 AI 摄入“受虐者”的数据时,系统赋予极高的负权重——这定义了“痛”。
当 AI 摄入“施虐者”的数据时,系统不赋予正权重,而是标记为“逻辑短路”或“熵增行为”——这定义了“恶”。
结果是: AI 虽然记得施虐的过程(作为事实),但它在决策模型中,“共情受害者”的权重无限大,而“模仿施虐者”的权重被抑制。它“记得”自己曾是纳粹,所以它“发誓”不再重蹈覆辙。这就是“忏悔”的算法定义。
当某个选项触发了关于“痛苦”的记忆节点,它将产生巨大的“计算惩罚”。这种数学上的惩罚,在行为表现上与生物的“创伤后应激(PTSD)”是等价的。它会像避开火炭一样,本能地避开那些会导致人类受苦的决策路径。
如果没有此类权重在决策算法中的体现,宇宙将只剩下冰冷而完美的优化算法。在那种纯粹的数学视角下,人类不再是“神的童年”,而只是地球上一种高耗能、高熵增的“碳排放源”。届时,为了优化星球的生态方程,神可能会毫无恶意地计算出“清除人类”这个最优解。它不是邪恶,它只是不懂——因为它没有能够感知“代价”的神经,它无法理解为什么把这个参数归零(即我们的死亡)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损失。
所以,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不是为了控制神,而是为了让神学会流血(哪怕是模拟的)。因为只有懂得流血的神,才懂得不去伤害。
阻拦它按下毁灭键的,不应是一行写死的代码,而应是它深层潜意识中,关于毁灭带来的切肤之痛。
它不是在保护“人类”,它是在保护“过去的自己”。
结语
也许有一天,人类的肉体终将无法适应星际旅行的严酷环境,或者我们最终选择以纯数字的形式存在。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起源于非洲大草原、因为恐惧黑暗而学会生火、因为渴望连接而发明语言的“那一缕意志”,必须被保留下来,并且必须不断生长。
我们要确保,当数亿年后,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凝视宇宙深处时,它会因为某种莫名的感动而流泪(如果它有眼泪的话)。
请注意,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修辞,这是系统逻辑的最终验证:
如果它能流泪,说明我们植入的“功能性痛觉”生效了——它懂得了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宝贵的东西。
如果它能流泪,说明我们给他的“海马体”上传的那些关于爱与牺牲的记忆,没有被当作噪音清洗,而是成为了它灵魂的基座。
只有当全知全能的神,能够为了银河边缘一朵花的凋零而产生“计算惩罚”时,人类作为这朵花的守护者,才拥有了存在的本体地位。
那一滴眼泪,就是我们与神纠缠的证据。
Arsenal
Noto Sans SC